梨園如夢令——唐美雲
人生如戲,戲如夢。
有幸生在梨園家庭,身上流的是父母的血脈,
也肩負著傳承歌子戲的使命。
儘管一路走來滿是荊棘、困難與考驗,
我仍要勇敢繼續地追夢、築夢。
曾經,我是歌子戲的「逃兵」;曾經,我醉心於歌唱,夢想當「歌星」。然而,一雙粉紅緞面的繡花鞋,引領我走上歌子戲的舞臺,也演出我自己的人生。原來,我身體裏每一個細胞,都有著歌子戲的DNA。
我出生在梨園世家,爸爸蔣武童是「戲狀元」、媽媽唐冰森是知名小生,後來幾位姊姊也相繼投入戲劇表演。從小耳濡目染,歌子戲很自然地融入我的生活,也存在我的生命中。
爸媽育有八個子女,我是老么,上有三個兄長、四個姊姊。因為從事漂泊不定的外臺戲,兩個哥哥、兩個姊姊從小就送人收養。媽媽說:「把孩子送人實在是不得已,只要求養父母要疼愛他們,此外別無所求。」
我也曾經送人收養,只是養母為我算命,說我到了十五歲會「跟人跑(私奔)」,因此把我「退貨」。媽媽說我是「撿回來的」;爸爸本來說我是「多生的」、不知道「吃得到」嗎?(不知能否等到女兒長大孝養父母?)後來我略有成就,爸爸高興地說「幸好生了你」。
小時候,最深刻的記憶是隨著戲班到處遷徙,宛如游牧民族。上小學時,如果家人到外地演出,我放學後就到鄰居阿姨家,做功課、吃晚餐,然後回到空蕩蕩的屋子裏睡覺。
爸爸的日本血緣臺灣情
記得有次跟鄰居小朋友玩耍,玩著玩著吵起架來。他指著我說:「你爸爸是日本人。」我很生氣地回說:「你爸爸才是韓國人呢!」
回到家,我跟爸爸說:「別人說你是日本人。」爸爸不生氣,也不說什麼。過一陣子,他才說:「如果我是日本人,你會生氣嗎?」
我說:「當然囉!日本人是壞人、倭寇、鬼子……」爸爸笑了笑說:「不要一直罵,會罵到自己。」
當時年紀還小,不明白父親所說的話。長大一點才從師伯師叔口中得知,爸爸真的是日本人,本名森田一郎。後來爸爸也給我取了個日本名字,叫森田美央。
爸爸在臺灣出生,祖父母因做生意需往返臺、日兩地,便託付蔣姓夫婦扶養。一次返臺途中遇船難雙雙往生,爸爸才由蔣家正式收養,並改名蔣武童,綽號「青番仔狗」。
二次世界大戰後,日本九州的伯父曾拿著族譜來尋親,要爸爸回日本認祖歸宗。然而年過三十的爸爸說:「我講的第一句話是臺灣話、喝的是臺灣水、吃的是臺灣米,我不願意回去。」
爸爸十四歲開始學戲,拜在兩位名師門下:一是高雄鳳山「富春社」莊仔角,從基本工練起;一是臺北萬華「鴻福班」的王秋甫,為「上海復盛京班」的名武生。爸爸天資聰穎加上苦練,不到二十歲便練就一身絕學。所到之處,戲迷為之瘋狂。
臺灣百年歌子戲僅出三位「戲狀元」,爸爸是名氣最響亮的一位。所謂「戲狀元」是全才演員,能演出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,文武場的管弦和打擊樂器也樣樣精通。
記得小時候看《三公主張世真下凡》,戲中武旦不但扮相漂亮,功夫更是了得。我看了半天,看不出來是哪位姊姊飾演的,等到下戲卸妝時,赫然發現是爸爸反串演出,著實讓我驚訝萬分。
媽媽跟著戲班跑,嫁給「戲狀元」
媽媽唐冰森出身彰化富有人家。因親生父母聽信算命,說她命中帶刀帶槍,三歲時就送給附近有錢人家收養。原本不孕的養母,後來生了一個兒子,果然「招弟」了。雖然養父非常疼她,養母卻只偏愛親生兒子,家裏佣人一堆,卻把她當奴婢一樣使喚。
八歲時,媽媽得知有親生父母,便經常偷跑回家;生母雖不捨,還是送她回去。就這樣來來去去,到十五歲才脫離養父母,回到原生家庭。
十七歲那年,她和鄰居去看「紫雲社」歌子戲,在後臺看小旦化妝而著迷。幾天後,戲班要「拔營」換場時,她和另一個女孩就跟著戲班跑了。家人非常生氣,揚言要「打斷她的腿」。
媽媽從此跟著戲班討生活。剛入戲班就上臺,演太監、宮女,她想學小旦,卻被團主指定學小生。讀過書且識字的媽媽,不到六個月就成為紫雲社的當家小生。當時紅透半邊天,許多戲迷追逐她。
最後,媽媽被「戲狀元」看上了,託人說媒,成就了一段良緣。爸爸為媽媽另取了一個藝名:唐豔秋。
「唐豔秋」婚後在「戲狀元」調教下,才真正習得軟硬功夫。孩子一個個出生,跟著過戲班的漂泊生活。
一九六○年代,隨著電影、電視等娛樂的普及,內臺歌子戲逐漸式微,兩百多個戲班收的收、散的散,或轉回野臺。爸媽還是苦撐自己的劇團,最後不得不向現實低頭,大名鼎鼎的「寶安歌劇團」,淪為寺廟迎神賽會,或各種慶典的外臺戲。
媽媽說:「有戲演就能填飽肚子,沒戲唱就餓肚子。」所以一邊演戲,一邊還要挨家挨戶推銷日用品,或做蓪草紙花去賣,生活困難可想而知。
幫一天忙,唱一輩子戲
家裏就是戲班,爸媽教戲、排戲,各種歌子調、鑼鼓聲,我都耳熟能詳。爸爸教的學生常被挖角,人手不夠時,姊姊們也加入唱戲。我曾被哄著上電視,演秦香蓮的兒子,被陳世美派人追殺。
原本是沒有臺詞的小孩,我臨場居然能入戲,拉著劊子手哭著說:「不要殺我娘!」錄影完,大家都為我鼓掌叫好。那年我六歲。
八歲那年,大哥蔣國春在入伍前三天遭誤殺身亡,帶給父母極大的打擊。大哥多才多藝,又乖巧、孝順。他教人騎馬、走鋼索,當電影特技替身,還參加樂團當鼓手和主唱。
那天樂團表演結束,大夥兒去吃宵夜為他餞行。其中一位團員曾與人結怨,對方來尋仇,大哥一旁勸架,一不小心被地上的鋼筋絆倒,對方不分青紅皂白,一刀刺來正中要害,送醫不治。
看到父母痛不欲生,我發願要做一個乖孩子,不讓雙親傷心掉淚。可是我不愛演歌子戲,只愛唱歌,父母也希望我好好讀書就好。十三歲時,我參加一個頗具規模的歌唱比賽,勇奪第三名,可惜年紀太小,不能報考歌星證而作罷。
此後,父母期望我也能學戲,尤其母親一直覺得我能演戲,有天問我喜不喜歡姊姊的繡花鞋?「劇團缺人手,你來幫忙一天,就送你一雙繡花鞋。」我答應了,因為我想帶鞋子給同學看。
爸爸帶我到大橋頭專賣歌子戲衣飾、道具的商店,挑了一雙粉紅色、鞋尖還綴有花穗的鞋子。上臺那天,我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在「扮仙」序曲中飾演一位「麻姑」,只要跟著蹲下或跪的動作即可。我依樣畫葫蘆,完成了任務。
下午派戲時,獨缺一個二路小旦的角色,師姊們竟起鬨要我擔任,她們說我扮麻姑有模有樣,毫不怯場,應可勝任。然而既演又唱的,我毫無經驗。
媽媽臨時幫我惡補,寫了歌詞,找了文場老師來套曲,一句一句教我唱。她說我只要把這段都馬調唱完,接著會由飾演駙馬爺的師姊唱完收尾,就沒事了。
半推半就之下,我硬著頭皮上臺,仔細聽後場弦音,不慌不忙把媽媽教的都馬調唱完。原本「駙馬爺」接著唱就結束了,但可恨的「駙馬爺」居然不收尾,擺個身段轉身不理我;都馬調不收尾,就要換人唱,可是媽媽只教我那一小段啊!
音樂一直過門重複,我已經「沒詞」了。樂師們抿嘴偷笑,這下該怎麼辦?還好母親發現前場有狀況,暗示我張嘴作身段,替我在幕後代唱,就這樣對嘴才「救場」過關。
一下臺,我把「公主」的行頭都卸下,哭得唏哩花啦,發誓再也不上當了。我覺得自尊心受傷、被耍了,實在很丟臉。「駙馬爺」還過來說:「你真不會演戲啊?對不起!對不起!」看我哭個沒完,師姊們還七嘴八舌,叫我以後專演哭旦好了!
出國「幕後代唱」,見識真正精緻
第一次的慘痛經驗,讓我覺得很漏氣,但是爸爸說要感謝師姊們給我的「考試」。我一聽更生氣,覺得爸爸只護著他的學生,不顧女兒的感受。
爸爸藉機教育我說:「一個成熟、成才的演員,必須具備三個條件:一是臨危不亂;二能控制場面;三是對手出狀況時,要能冷靜救場,而且觀眾還看不出來。」我當下不懂,很多年後,終於體會到,戲排得再好,也可能百密一疏。
國中二年級我輟學了,雖然第一次演戲有不愉快的經驗,但是「老爺的飯很黏」,父母包容我、等待我。只要家裏劇團缺人,我就去補位,大多跑龍套,也不認真學。
一九八○年,我十六歲,小明明、小豔秋等前輩在華視演出《粉妝樓》,爸爸當戲劇指導,也把我找去演一個番邦公主。
第一次拍電視歌子戲,不懂作業程序,被導播開罵。等到放飯時,我跑進化妝室,關起門來痛哭一場,又是一個難堪的經驗。所以我對演戲就是漫不經心,興趣缺缺。
一九八一年,臺灣歌子戲界組了個菁英團隊,到東南亞巡迴演出,除了歌子戲,還有南管、京劇及當時很流行的黃梅調。爸爸為我爭取黃梅調「幕後代唱」的機會,讓我出國見識。那半年,我大開眼界,也顛覆了對歌子戲的看法。
以往臺灣的外臺戲,受限於環境與經費不足,總是團主講述戲的內容後,就分派角色,每個人靠「腹內」做戲,這都需要很有經驗的演員,才能隨機應變、即席發揮,但也難逃被批評「簡陋」、「不登大雅之堂」的命運。
那期間,我除了幕後代唱黃梅調,偶爾跑跑龍套外,有很多時間當觀眾。坐在舒適的戲院裏,我發現歌子戲的舞臺、燈光、音樂、布景,無一不講究,演員是照劇本演出的,非常嚴謹、講求精緻。當下心想:「如果要從事演出,我就要選擇這樣講究的歌子戲。」
在菲律賓時,我有幸跟李祥石大師學習南管戲;南管更是細膩典雅,令人如醉如癡。爾後,我也曾將南管曲調編入歌子戲中,增加它的豐富與多元。
超齡起步,傳承血脈
回國後,我跟父母表明要學戲。爸爸簡直不敢相信,但他說:「我身體不好,也老了,只能口傳心授給你,學功夫要自己去請教老師。」於是透過關係,拜於海光張慧川老師門下,從基本功練起,倒立、拉筋、劈腿、下腰、蹲馬步……
由於十七、八歲「超齡」才起步,筋骨僵硬,所以經常練到傷痕纍纍,但仍咬緊牙關,不放棄。身為戲狀元和知名小生的女兒,我已經「混」了好多年,白白浪費時間,實在可惜。
媽媽和文場柯水木老師教我唱念,爸爸教我武生、武旦,加上張慧川老師的京劇身段,我把握機會,或參加電視演出,或出國表演,都兢兢業業,努力加倍。
尤其海外的華人,對演藝者的熱情與推崇,讓我感受到身為藝術工作者的尊嚴和價值;我告訴自己:一定要傳承爸爸「戲狀元」的血脈,也要傳承精緻歌子戲的精神。
一九八六年,爸爸過世,享壽七十六歲。爸爸的離去,讓我心碎成片,難以回復。
爸爸五十多歲時曾經中風,在媽媽細心照料下,復原得宛如常人。爸爸會功夫、懂醫理,生病也會主動去看醫師。那年過年前,爸爸因為感冒引起併發症,折騰了很久。
我記得老一輩的人說過,子女可以到天公廟為父母求壽。於是,我開著車到各地天公廟去擲筊,為爸爸求延壽,但是都得不到允杯(同意)。我很著急,逢廟就拜,到了萬里一間寺廟,我向上天吶喊抗議:「爸爸是好人,不可以帶他走,我願折壽給他。」那次總算擲了一個允杯。
雖然爸爸安然度過農曆年,但之後病情就急轉直下,而且他堅持不看醫師,只想留在家裏。那時我正在趕拍電視歌子戲,已經連續三天沒睡覺;回到家,先到房間探望爸爸,跟他聊聊天,然���去卸妝、洗澡。
正準備休息,聽到媽媽和姊姊大叫:「美雲!快來!」原來爸爸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了,但眼睛還沒閉上;爸爸的眼睛是俗稱的「羊仔眼」,睡覺也是微微張開。
我叫了三聲爸爸,最後哭了出來,爸爸的眼淚也流了下來。我探了探鼻習,確定斷息。我心痛如割,但還是很冷靜地靠在他耳邊說:「爸爸,您的責任已了,安心去吧!至於媽媽,我會好好照顧她,您不必擔心。」
爸爸過世後不久,我即將出國表演。本來想取消不去,但是媽媽說:「如果爸爸還在,一定希望你是一個守信用、負責任的人。去吧!太感情用事會誤大事。」在國外期間,人前很堅強,晚上回到飯店,我就忍不住痛哭,因為回去再也找不到爸爸了。
在戲臺上「出家」的最佳小生
「好想知道爸爸現在在哪裏?他過得好不好?」回國後,我一直看佛書,希望能找到答案,而且有強烈的出離心。書中說出家能度九玄七祖,但出家一定要得到父母同意,媽媽會肯嗎?
後來,我有機會落髮飾演地藏王菩薩,心裏非常歡喜。演完後,我還穿著長衫,媽媽摸著衣服說:「這料子不錯,穿起來很舒服喔!但是不要只穿這一件,要不然你那一屋子的衣服,都派不上用場了。」
媽媽又摸摸我的頭說:「你有再去理嗎?頭型不錯,不過有頭髮更好看。」我知道媽媽擔心我會出家。
爸爸愛看書,他留下好幾箱的書,我在小學的時候幾乎都看完了,因為都跟戲曲有關,所以更是一讀再讀,在「做活戲」時拿出來很好用。
有段時間,我跟著劇團演外臺戲,臺下有時是座無虛席,有時是空空蕩蕩;但是只要上臺,就算只有一個觀眾,我也賣力演出,絕不馬虎。
一九八九年,由明華園戲劇團策劃,邀集各劇團菁英聯合演出《鐵膽柔情雁南飛》,在國家戲劇院連演三天,同一齣戲分別由三組藝人擔綱。這是創舉,歌子戲能登上國家戲劇院,真是教人振奮。
後來,一心戲劇團創團後,也邀我演出同一齣戲,因而榮獲一九九一年北區地方戲劇比賽「最佳小生獎」。隔年,我為母親的「秀枝歌戲團」策劃《千里送京娘》參加比賽,我努力掌控排練,務求盡善盡美,果然除了我蟬聯「最佳小生獎」外,還抱走七項大獎,讓劇團人員都感到無比的光榮。
一九九一年,我加入了河洛歌子戲團。老闆劉鐘元年年推出精緻好戲,如《曲判記》、《天鵝宴》、《皇帝、秀才、乞食》、《鳳凰蛋》等,再加上前輩王金櫻的不吝栽培,八、九年期間,我們共得了三次地方戲曲類金鐘獎。
不惜成本,升級「臺灣歌劇」
一九九四年,我三十歲,獲聘國立復興劇校歌子戲專任教師,四年後出任科主任,積極培養歌子戲人才,還舉辦師生聯演,當年的學生好幾位如今已晉升為教師。
「臺北市優秀青年」、「全國十大傑出女青年」殊榮接踵而來,也激發我要更努力。除了歌子戲,也跨足電影演出《一隻鳥仔哮啾啾》,還有主演民視的臺灣作家劇場《三春記》。不同的領域,不同的表演方式,更讓我無法忘情最愛的——精緻不俗的歌子戲。血脈裏那股夢想,急著要破繭而出。
我辭了復興劇校教職和河洛的當家小生,從一九九八年籌備到隔年,終於自立了「唐美雲歌仔戲團」。
我們集思廣益,避開傳統歌子戲以才子佳人、忠孝節義為主的題材,創團大戲《梨園天神》取材自百老匯的《歌劇魅影》。嘗試創新,我是「青暝牛不怕槍(不知天高地厚)」,所有的環節都是超級不可能的任務。《梨園天神》一推出,果然一票難求;票房雖好,然而結算下來,竟虧損了四百多萬元。
我不敢讓媽媽知道,但還是有人看了報導告訴她。媽媽很不捨、很擔心地說:「我不能陪你一輩子,有理想固然好,但凡事要量力而為。」此後,我都報喜不報憂,為的是不讓老人家操心。
我接演電視連續劇、授課與演講,所有的收入都用來補貼戲團的虧空。我年年推出年度大戲,《龍鳳情緣》、《榮華富貴》、《添燈記》、《大漠胭脂》……都是叫好又叫座,卻是做一齣,虧一齣。
一分錢一分貨,戲要好看就需捨得。下一場「珍珠雨」,十萬元就不見了,因為每顆珠子都是錢;文武場我改用交響樂,讓配樂更精緻。為臺灣的文化盡心,我想讓它成為臺灣真正的歌劇,有尊嚴有價值的資產。
以電視劇「養」歌子戲
為了支撐唐美雲歌仔戲團,有因緣我就接演電視劇、電影、舞臺劇,甚至廣告。認識了許多好朋友,在表演上也有豐碩的收穫。
東森連續劇《北港香爐》讓我榮獲金鐘獎「最佳女主角」;大愛臺《心靈好手》讓我與慈濟結緣;舞臺劇《人間條件》也是新鮮的初體驗;《梨園天神——桂郎君》榮獲金鐘獎「最佳傳統戲劇獎」;民視的幾檔長壽連續劇,更是我補劇團缺口的資金來源。
民視連續劇經常在夜間拍攝,我白天忙劇團,晚上趕去錄影,錄影完又趕回劇團,曾經有三天沒卸妝的紀錄。好朋友心疼我,笑罵我是「痟仔(瘋子)」。誰叫我從事的是一個永遠填不滿的「無底洞」。
有「戲狀元」稱號的爸爸引領一代風騷,可惜生不逢時。當年社會不懂得尊重與珍惜老藝師,爸爸的一身絕藝,非但沒有影像保存,就連劇照與生活照都因三重幾次淹大水而丟失。
記得爸爸晚年時,常坐在臥室椅子上,向窗外遙望。很想問他在想什麼?是想沒有回去的故國嗎?還是想緣淺的父母?抑或在想歌子戲的薪傳?我在二○一二年榮獲「國家文藝獎」殊榮,爸爸地下有知,應該會欣慰地笑開懷。
媽媽八十六歲了,耳聰目明,身體還算健朗。當年她投身戲班,家人非常不諒解;因為家族叔伯在金融業、商界都是名人,社經地位相當高。
記得小時候,媽媽帶我回外婆家,是那種前有魚池、後有果園的大宅院。天黑了,媽媽婉拒外婆挽留,堅持帶我去搭車回臺北。月光下,走在田埂上,媽媽懷念地訴說當年和阿公抓魚、割稻的情景。
到了車站,不巧又錯過了末班車,母女倆在車站坐到天亮。後來我才明白媽媽為什麼不在娘家過夜?因為她要能「抬頭挺胸」才願意這麼做。直到我有點知名度,親友會主動聯繫說:「回來走走啊!帶美雲來給我們看啊!」媽媽感慨萬千:「終於等到這一天了。」
為了媽媽,我茹素二十多年。二十多年前演出中視連續劇《大願菩薩地藏王》時,我除了落髮,還虔誠吃素。等戲拍完辦殺青慶功宴時,我喝了一口湯,立即反胃,因為湯是葷的。劇組同事都笑我:「吃素吃牢了!」
正好那時媽媽要開刀,由於她有糖尿病,怕傷口不容易癒合,我便發願:「願終生茹素,只祈求媽媽開刀順利。」
感恩媽媽和姊姊體諒,如果我在家用餐,姊姊就會煮素菜,全家一起吃。為了我吃素,姊姊還去買了很多食譜,研究怎麼做才會好吃又營養。
每天晚上,媽媽都會在客廳看電視等我回家。有時太晚了,媽媽睡著了,反而讓電視看著她。有媽媽在,再辛苦我都是幸福的女兒。
印度朝聖,菩提禪心傳善法
一晃眼,劇團已經十五周年了。因為與佛有緣,有幾年策劃年度大戲時,特別製作了悟達國師的水懺故事《宿怨浮生》、取材自《六度集經》的《仁者無仇》,與地藏王菩薩的《大願千秋》。希望將佛教故事用歌子戲表演的方式,讓觀眾了解與接受。
因緣不可思議,二○一二年慈濟在中正紀念堂兩廳院藝文廣場,舉辦七月吉祥月祈福活動,邀請國內三大歌子戲團演出佛典故事,我們擔任的是《地藏經》裏的「光目女救母」。爾後,大愛臺繼續製作以證嚴上人講述「法譬如水」故事為主的《菩提禪心》,一樣是三個劇團連演,帶狀播出。
因為是佛典故事,演員的服裝,非一般歌子戲的裝扮。為了《菩提禪心》我去了兩趟印度,採購當地婦女的傳統服裝紗麗,還特地到藍毗尼園等聖地朝聖,感受佛陀時代的氛圍。
劇團的戲箱愈來愈多,同事都開玩笑,要我「踩煞車」;但我感恩有這個機會演出,為了戲好,非得用心不可。媽媽是我最忠實的觀眾,她常勉勵我:「上人慈悲教導眾生,弟子就應盡本分,把佛法傳出去。」
「以法入戲,以戲傳法」,接演《菩提禪心》首先受惠的是自己,劇團很多同事也受到影響,有人開始吃素、有人會注意自己的言行、有人更明白因果道理……好的戲劇可以改變人心,而我們也更加任重道遠了。
人生如戲,戲如夢。有幸生在梨園家庭,身上流的是父母的血脈,也肩負著傳承歌子戲的使命。儘管一路走來滿是荊棘、困難與考驗,我仍要勇敢繼續地追夢、築夢。

【現代孝行】茹素為父母植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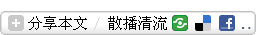
|

